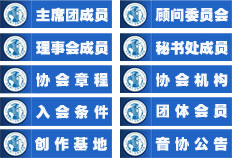中国蒙古人和在蒙古国居住过的华人普遍都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蒙古国的音乐要比中国音乐好听,当然也要比在中国乐坛占有小半片天空的内蒙音乐人创作的乐曲旋律要更加动听一些。
一位中国著名音乐人评论说:从2005年的《吉祥三宝》起,中国就再没有什么流行音乐。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也红了半年之久,至今,中国人的手机铃声还保留着这两首曲目。而也许是由于华人的本性和欣赏品位的原因,《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恶俗歌曲也占据一方乐坛。原本蒙古音乐和华人音乐结合本身就非常的融洽,远比藏族音乐、维吾尔音乐与中华民乐结合的要融合得多。像《月亮之上》《敖包相会》《蒙古人》等等歌曲在华人的视野中早以脱离了“少数民族”这样的定位。但是内蒙的音乐人却不断的在翻新内蒙蒙古族民歌中加入风声、雨声、马的嘶鸣声、狗的咆哮声、长调、呼麦……,能加多少加多少,越“原生态”越好,越乡土气息越好,越“少数民族”越好,只要是创作蒙古音乐必将马头琴作为配器,以达到“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这个定位,这个定位很明显是将华人群体作为主要受众群体,而这种定位的音乐往往很难敲响蒙古国这个蒙语歌曲市场,蒙古国音乐人更喜欢把内蒙民歌按照本国特色重新编曲演唱,去掉马头琴的声音(蒙古国马头琴一般在民族器乐演奏或原生态传统器乐演奏中应用),换上二胡、雅托克、钢琴、提琴、吉他等等打造成蒙古国流行音乐风格的民歌。
中国一支在国内数一数二的蒙族乐队在去蒙古国开拓蒙古语音乐市场无功而返,原因是蒙古国优秀的乐队,在世界流行乐坛都能排得上名次,比如HURD乐队和Haranga乐队,Hurd乐队更是公认的亚洲最棒的乐队。内蒙的乐队只能算是二、三流的乐队。蒙古国民普遍接受的音乐风格也和中国不同,蒙古国的摇滚乐、R&B、重金属组合基本上是段段都是经典,而主唱的声线条件也非常优越。中国的蒙古乐队如果想在蒙古国乐坛站稳脚跟往往比在中国国内靠唱汉语带点儿蒙古味儿的歌要难得多。凤凰传奇在华人乐坛风光了一、两年,也算是半支蒙古乐队,但没有几个中国蒙古人了解他们的作品,因为一般都是华人在听。最受喜欢程度高的黑骏马组合、阿吟琴乐队、蓝野乐队、五支箭乐队、达尔汗乐队、苏力德乐队这些以蒙古语为主要演唱语言的乐队组合其主要歌迷群体也是内蒙的蒙古人,其选唱曲目有翻唱内蒙民歌、翻唱蒙古国或卡尔梅克歌曲、原创歌曲等,有些歌曲有蒙、汉两个语言的版本。而今年声名雀起的额尔古纳乐队早年翻唱的巴彦淖尔民歌《鸿雁》被《东归英雄传》选做主题区奠定了额尔古纳乐队唯美风格的蒙古族民歌走势。零点乐队一直以来是华人乐坛中一支重量级乐队,也是内蒙古的乐队,主要定位是华人摇滚音乐,也翻唱少量的内蒙民歌。安达组合、吾博组合、江格尔宫廷古乐团主要是走纯原生泰的发展路线、主要擅长演唱长调、呼麦,弹奏胡琴、火布思、雅托克、蒙古扬琴、胡笳和马头琴等。
中国和蒙古国歌手相互翻唱对方的歌曲都为数不少,其中中国歌手翻唱的主要是蒙语歌曲,有巴特尔道尔基翻唱蒙古国吉布呼楞的歌曲《远方的母亲》、黑骏马组合和德德玛翻唱的蒙古国作曲家赞庆诺日布的《远去的母亲》、其其格玛和英格玛都翻唱蒙古国阿茹娜的《草原蒙古人家》、莫日根翻唱过蒙古国斯日其玛的《梦中的母亲》、阿穆隆翻唱过蒙古国Hurd乐队的《母亲》、haranga乐队的《思念》、成吉思汗乐队的《乌兰巴托之夜》、蒙古国歌手宝力道的《我的R&B》和阿茹娜的《爱的滋味》等。蒙古国翻唱中国歌曲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内蒙蒙族民歌重新编曲演唱注入蒙古国特色,使那些走半蒙不汉路线的经典民歌改编成地道的蒙古韵味民歌,甚至是改编成喀尔喀风格的民歌,比如《万丽》和《云登哥哥》等。另一类是翻唱华语歌曲,有陈小春的《算你狠》、许茹芸的《独角戏》等等。
内蒙优秀的作曲家很多,但作曲方向也是本着华人音乐这个趋势去创作的,比如斯琴朝格图的代表歌曲作品《蓝色的蒙古高原》、《我和草原有个约定》、《阿妈的佛心》、《心之寻》,《泡泡雨》、《爱的哈达》,《心中的故乡》等等。乌兰托嘎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天边》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色•恩克巴雅尔的《吉祥的那达慕》;阿拉腾奥勒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都是将汉语歌曲作为蒙古音乐的首选语言创作的。其中由蒙古国歌手斯日其玛演唱的歌曲《心之寻》从音乐响起就带有浓厚的中国味儿,使人联想到一定是出自中国蒙古族作曲家的作品。而三宝、道尔吉等擅长创作电影音乐的作曲家更是在《嘎达梅林》、《悲情布鲁克》等电影中表现出了创作蒙古音乐的天赋。
很多人常说蒙古国音乐至少比中国先进20年,其实中国音乐与蒙古国音乐相比确实逊色了许多,好作品很少,编曲和配器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中国的蒙古音乐如果不及早摆脱错误的定位也难有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