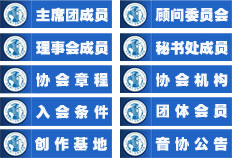华人文化中的音乐,有非常多对大自然之景的描述。而且,这种对大自然的描述,往往与华人传统中之读书人的思想最密切相关,也具有最多重角度的诠释。
我们先来分析不同的几种诠释,並其与传统读书人思想的关连性。
一.透过乐器属性表达山水的自然面貌
譬如王巽版本的高山流水,透过古箏乐器的"金风瑟瑟"特质,先出之以沈厚音感表达高山之巍峨稳重如故乡,然后用弹骨干之拂音,表达流水潺潺之态。其山水之感不仅微妙微肖,而且让聆听者被带入心境祥和与人无爭的情境中。
另外一例,就是国乐中有非常多的对鸟类的描写,诸如《雀踏枝》,《百鸟朝凤》,《海青歌》,《鹧鸪飞》,《凤凰展翅》,而刘管乐先生改编的笛子曲《荫中鸟》,充分运用历音(从某一音起快速演奏的一段级进装饰音),滑音,吐音等技巧,表现活泼欢快一派生机,的确让人有进入森林之感。
这类对大自然极尽传神的模拟,其实是人类共通的对大自然的皈依需求,人类內在深处一直就有与天地融合的渴望。
但这样描述下的大自然之音,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之作为主体並不存在。人彷彿是隐形的,单单把大自然之音倾注而来,让听者置身於浩瀚之中。
这种人之作为主体消逝於大自然之音的呈现,卻衍生出其他种不同的诠释。
二.透过大自然,表达君子心
这跟华人经常以大自然景物传达君子心很有关系。譬如梅、竹、莲、松柏……。
这类的自然之景,诸如《出水莲》,曲子立意是表现清淡,典雅,因为莲花为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托物言志。《梅花三弄》,曲子表现着重孤高清冷刚毅,因梅花为花中之最清,一样有譬喻之意。
这种从大自然之音走向君子心,最明显的莫过於《高山流水》此曲的多重意境诠释。
《高山流水》,琴与箏与琵琶都有谱传世。光就箏曲,至少也有河南与浙江两大地域之別。这不奇怪,因为人冀望与大自然合一,乃古今中外皆然的普遍心灵状态。

所以中国之诗,抒大自然之景的,远比抒人世际遇的,更易在年纪很轻时就臻成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李白二十多岁就创作出来的名句,跟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之名句齐名。
但更多《高山流水》对山水之音不多雕琢,是在着意纯朴宁靜,旷远雅逸,企图折射出"峨峨兮若高山,洋洋兮若流水"的君子之志,因此乐曲之诠释清冷空灵,毫无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绪,恰似山高水长,浩然天地间淡泊名利。这种毫无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君子志,到底算不算有人/主体的存在呢?
很矛盾的,《高山流水》仅管曲风清冷,卻常於文人雅士朋友聚会时弹奏,原因在於高山流水的典故:
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泽泽乎若江河。"
其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是个悲剧,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
钟子期是生命之终,伯牙是心灵之死。
而《高山流水》点到山水之音与君子之志,卻未点出子期之死与伯牙之心碎,便走入清冷之君子志。
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这第二点对大自然之音的诠释,出现君子志的影射,但还是以大自然为本的,人向大自然的赋归,人之成为主体还是十分不明显的,因此情感隐藏,音色清冷。
为何会这样呢?
因为在华人文化的思维模式中,很重视人格修养的养成,先有个体的道德人格,方有社会道德甚至是政治能力,而这个体道德又跟靠修练必能达至的人性本善文化特质有关。这种人格修养,还包括"参天立地,居天下之广居"。所以透过自然隐喻君子之节,就是很自然的一种进程了。这种君子气质,基本上着重清冷,无大喜大悲。因此尽管描述伯牙钟子期,还是点到君子志,不描述生命之终与心灵之死的悲涼情感。
其实华人对自然界,其实是有着一种矛盾的情感的。主要的原因是,修养需要有一种评定的标准,礼法,往往是社会借以审视修养的重要方式。华人的道家思维,便是透过自然,企图反抗社会约定俗成的礼法。其理乃是:礼法出自人为,自然界超然。所以自然界成为反抗,超脫的方式。
於是又出现第三重大自然之音的诠释。
三.透过大自然表达一种近似宗教的情怀
对华人而言,道家思想几乎已渗透进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与儒家思想並存的一种思维模式。儒家讲究礼法秩序,道家则透过对大自然的参赞超脫礼法秩序,前者重视社会规范,后者重视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渴望,已经从享受与自然界的融合,进至借助大自然解脫现世,以超时空,超善恶,超爱憎,超生死意义的逍遙遊。从此适性得意,以山水自娛,退居自然状态的原始本然中。
在这种情況下,国乐中的山水之情,就从"孤高清冷"再转至"逍遙适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丝竹乐《春江花月夜》。这首名曲若以琵琶演奏,就变成《夕阳萧鼓》。曲子呈现月,风,花影,水云,最后透过渔人歌声,点点白帆,江岸翻卷,将宁靜,逍遙,超脫的意境呈现的淋漓尽致。
在这种类型的大自然之音中,人之作为主体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彻底的融入与逍遙,完全掙脫生老病死的哀愁,只视之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作为主体也完全超越社会礼法的规范,这用华人文化中另一个名词,就是君子之隐逸。
描述大自然之音,到这里,已非常贴近宗教情怀—逍遙适意的人生观了。
如果大自然之於人,是完全的适意逍遙,境界何其高远超脫!但在国乐中,大自然卻还扮演第四种功能…
四.透过大自然抒发不平
这第四种对大自然之音的诠释,就有強烈的人之主体性格的出现。
譬如说箏曲《寒鸭戏水》,若只取题,一定马上想到在水中逐戏的鸭子。但按原版,曲速三变,由三版,二版到烤拍等三个先慢后快的段落,这种速度对比,加之"重三调"端庄深沈的调式,分明是在对人生作一种严肃的思考,而且心有所感不得不吐的成分很重。
国乐一如诗,往往借景喻情。标题写景,音乐卻写情。
这类的借景喻情,人之作为主体就很明显的浮出於大自然,成为音乐的主角。
大自然,不过是配衬而已。甚至可以说,大自然反过来融入了人之意志与情感。类似的曲子,还出现於古琴曲《幽兰》,借兰描述郁郁不得志之感慨,或琵琶曲《大浪滔沙》,以其最后长轮转入低音弦的滑揉並双音,呈现心未能止的感慨,是标准的借景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苍涼心境。
当然,华人音乐中,还有很多节庆婚丧的曲调,或描述民间生活色彩的诸多曲目,或宮词闺怨,或千古离情,但这都完全以铺陈历史,社会,人世,情感为主的,並不涉及自然景观,而这类曲子要不就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要不就是哀怨的独白,彷彿用乐器把苍涼哀怨唱给一个无法改变现状的,充满无力感的对象。
所以我们会发现,像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第六、七、九交响乐这样人之作为主体非但不融入自然,甚至刻意強烈的浮出於自然之外,並与自然对抗的音乐描述,或者像如贝多芬后期音乐,在自然之上另有"他者"作为主体,人与"他者"直接产生对抗,控诉,吶喊祈求,或人邀请"他者"进入陪伴观照己心的音乐描述,可以说,完全不是华人文化的基调,当然,也就很难在华人的艺术中找到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