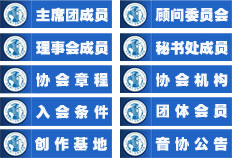钢琴家郎朗享有的全球声望,让他在自己选择的一家巴黎中餐馆接待我时,让我感到一些慌乱。当我提出已经以郎朗的名义预定了座位时,女服务员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接着我被领到餐厅前面的一张小餐桌前,我担心我在拼读郎朗的名字时把音调搞错了——在讲广东话和普通话时,音调至关重要。尽管这两个词在英文中看上去一样,但在中文里,他的名寓意“快乐和阳光”,他的姓寓意为“受过教育的绅士”。
17岁成名
令人高兴的是26岁的郎朗很快就到了,以他浮华的标准来看,他今天的装束相当严肃,黑色夹克,黑色衬衫还有牛仔裤。他名誉的光环以及友好彻底改变了局面。餐厅经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并领我们走到了餐厅后面的一张餐桌前,一扇竹木屏风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私人房间的效果。这是北京和上海所有高级餐厅的设计。我问他,他是否觉得在中国外出就餐很难,因为他是如此的著名。他回答:“极其困难,这既是幸运,也是不幸。”我后来意识到,这番话反映了他成为一位著名钢琴家冷静的处事方法。然而,他可能很久不在中餐馆点菜了,因为我们那张小方桌上很快就堆满了烧茄子、甜玉米羹、美味的京酱肉丝以及一壶茉莉花茶,食物还在不断端上来,以至于我的笔记本几乎都没地方放了。
上菜的速度赶不上郎朗的筷子在盘子间跳跃的速度,他好像在指挥一个管弦乐团,他手法敏捷地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次,他夹起一块我掉在笔记本上的猪肉,把它放到了旁边的盘子里。他隔一会就责怪我光顾着记录,却没有吃菜。)他说道:“这家餐厅非常好,每次我到巴黎都会与朋友和亲戚来这里吃饭。”他来到伦敦是为了参加一场音乐会。我刚刚乘坐欧洲之星(Eurostar)从伦敦赶来与他会面。我告诉他,几年前当我第一次从香港搬到伦敦时,我一直在伦敦西区Queensway附近找房子,因为当地的餐馆能够提供一些伦敦最好的中餐。
有段时间,我一直在摆弄我的数字录音机,他忍不住开玩笑说“它肯定是英国制造”。这是对人们有时取笑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的反驳。
中国出口商已开始走向市场高端,郎朗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最为人熟知的面孔之一。他第一次受到世界的关注,是在1999年芝加哥附近的拉维尼亚(Ravinia)音乐节上,那是一场神话般的首演,当时17岁的他顶替安德列·瓦兹(André Watts),站在1.7万名观众面前。演出前一天晚上,他曾梦到他的钢琴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环绕地球”。当他演奏完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气势磅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后,获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此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演出结束后,聚集在一起的音乐大师们,包括指挥家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该音乐节的音乐总监以及其他人,邀请他在凌晨2点后开始的私人演奏会上背谱演奏了难度很高的巴赫(Bach)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
10年过去了,郎朗曾与奥迪(Audi)、万宝龙(Montblanc)和索尼(Sony)和阿迪达斯(Adidas)等品牌签约,他经常被视为一位跨界明星,一位有着摇滚明星吸引力的古典音乐家。(阿迪达斯现在销售的一款印有郎朗签名和金色条纹的训练鞋售价125美元。)他曾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Beijing Olympics)开幕式上演奏,他在东西方有着无数的追随者,在YouTube上,他的视频广受关注。如今,超过3000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弹钢琴,钢琴如此受欢迎至少要部分归因于郎朗如日中天的事业。
普及古典音乐
录音机终于恢复正常了,我问他关于本月的音乐会系列以及与伦敦交响乐团(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的计划。他对4月18日举行的大师班尤其感到兴奋,该活动的高潮将是他为来自伦敦东区学校所有等级的100位钢琴家演奏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March Militaire)。这是他在几个城市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让年轻人从音乐中找到乐趣。
“我发现,问题是我们的工作的形象。人们认为,我们是非常枯燥的人:从不说话,像机器人一样,而且非常傲慢。(他们认为)我们是精英。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只是一般人。当我们走入每一所学校时,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第一点,要鼓舞他们,然后说‘看,我们是正常人。'”与学生的年龄更接近也会有所帮助:“许多父母说,‘你能跟我的孩子说些什么吗?因为如果你说什么,他们会听。'如果你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优秀的知识,那么与年轻人分享很重要。”
郎朗非常热衷于努力普及古典音乐。对于一个每年以每场约5万美元的出场费参加多达130场音乐会(这些数据发表于《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的人而言,他仍花费很多时间走入校园。去年11月,他创办了郎朗基金会(Lang Lang Foundation),以推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音乐教育。他还是万宝龙文化基金会(Montblanc Cultural Foundation)的主席,该基金会为艺术赞助人提供1.5万欧元,以捐赠给他们青睐的文化事业。
他这种对教育的关注并不意外。郎朗的自传《千里之行》(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将于下周在英国出版,本书可能会被称为“与一千位老师的旅程”(Journey with a Thousand Teachers)。在他人生中的几乎每一步,老师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82年6月,郎朗出生在中国东北城市沈阳。他的母亲是一名电话接线员,父亲是一名警察,但却拥有音乐才能。郎国任拉过二胡,在郎朗3岁那年开始让他弹钢琴。4岁时,郎朗师从音乐教师朱雅芬。朱雅芬自己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时期自杀,当时西方古典音乐家曾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她留给朱雅芬的遗产是巴赫和莫扎特(Mozart),然后朱雅芬又将其传授给了郎朗。郎朗回忆道:“她是一位优秀的启蒙老师。问题是,懂得如何演奏巴赫的中国老师并不是很多。她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教授如何弹奏巴赫作品的老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遗产。他解释道:“许多老师都是在前苏联接受的俄罗斯曲目的训练。”
朗朗的自传
郎朗9岁时,他的父亲辞掉工作,带儿子来到了北京,因此郎朗才有可能攻读北京最具声望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父子俩每月依靠郎朗的母亲从沈阳寄来的150美元生活,他们住在一间冬天没有暖气的房子里,他的父亲晚上要先钻进被窝,给儿子暖床。生活很艰难,父子俩曾因为练琴的时间发生激烈争吵。一天他父亲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嚷道:郎朗应自杀,而不是给家里抹黑。之后这个倔强的孩子4个月拒绝练琴。
郎朗的自传读上去像是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父子间的矛盾终于化解,一位卖水果的人帮助了不快乐的孩子,并鼓励他继续弹琴。当时在美国任教归来后,郎朗的启蒙老师朱雅芬意外造访父子在北京的家。她安排郎朗与一位教授合作,这位教授让郎朗做好了在第二年夏季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准备。
这部自传详细描述了他父亲的愤怒和霸道,但却献身于他和他的妈妈周秀兰。我说道,这部自传最后的闪光点是父亲对儿子的那种望子成龙式的爱,而非美国读者关注的父亲的愤怒。本书于去年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人们很难理解。但亚洲人却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
郎朗告诉我,他父亲曾经告诉“一名(中国)记者,这本书让他深受感动,因为他认为这表明我已长大。我感到很自豪,因为他没有感到伤心或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觉。”
1997年,15岁的郎朗得到了赴美、从师于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的奖学金,格拉夫曼自己的事业因为他的手受伤而被迫中止。与其他在费城颇具声望的柯蒂斯音乐学院(Curtis Institute)学习钢琴的学生一样,郎朗有了自己的一间公寓,他与父亲合住,公寓里还有一架7英尺斯坦威钢琴(Steinway)。在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夜里,郎朗在睡梦中醒来,走过去摸了摸那架钢琴,以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感觉就像是到了天堂,”他回忆道,往事似乎历历在目:“那是全世界最小的学校。整个学校就像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班。在中央音乐学院,你会看到5个或6个人因为一架小小的、愚蠢的立式钢琴而竞争。要想弹钢琴,必须先得到入场券。”
尽管拥有柯蒂斯和朱利亚音乐学院(Julliard)等名校,但郎朗表示,音乐教育的危机出现在美国,而非中国。伦敦和纽约的古典音乐听众似乎正迅速老化,而在台北或香港,古典音乐听众的平均年龄有时似乎只有10岁左右,这可能反映了亚洲的进步。郎朗回答,在美国,预算赤字意味着“他们首先削减的是音乐和艺术开支,许多学校不再设立音乐课。没有任何真正教授如何聆听贝多芬(Beethoven)和莫扎特的培训。(这好像是)你是一名学生,但却不学雨果(Hugo)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你不可能指望,一位从未听过古典音乐的人在30岁时突然开始去听这样的音乐。”
尽管郎朗技艺娴熟,但他一直因为演奏时有些“情绪放纵”而受到批评。从某种程度上为了帮助克制自己,他邀请指挥家兼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以前也是一位神童——担任他最新的导师。(郎朗在与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以色列音乐家首次会面时就向其请教。)郎朗每隔几个月就会去拜访柏林的巴伦博伊姆。“他教给我如何控制自己……不要让情绪控制知识。但关键是,你必须有幻想,否则所有人弹的都一样。”
午餐结束了,餐桌很快被收拾干净——葱爆羊肉、中式炒鸡蛋以及油炸馒头几乎都没动过就被撤下了,然后是一大盘外国水果,我们刚吃了一点,就到了郎朗该离开的时间了,他要稍事休息,然后参加当晚的音乐会。
与郎朗交谈的话题漫无边际,从北京在主办奥运会后转型为一个外向型城市,跳跃到2009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郎朗曾帮助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为受灾者筹款。我问起了维权人士黄崎的境况——地震中,由于劣质校舍倒塌,有上万名学生遇难,黄崎因支持其中一部分学生家长上诉而被捕。郎朗表示自己不知此事,从而略过了这一政治问题;作为中国的一名超级明星,他可能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很不明智。
郎朗开朗的形象并未受到影响,开始讲他以前的老师格拉夫曼(Graffman)的一件趣事。“我们在纽约时就住对街,并一起参加聚会。”郎朗用手机为格拉夫曼的公寓拍了一张照片,并发给了他。格拉夫曼立即回电,“他说:‘教我,教我(怎样拍照)。'他确实很可爱。81岁了,还非常喜欢科技。”郎朗不费力就把美国俚语和不拘礼仪与中国尊师的传统融合在一起,这令人难忘。如果这就是全球公民之所指,那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